作者:侯賀奎
秋風(fēng)起,“霜降”至,兩場(chǎng)霜雪落過,大地上的紅薯葉由綠變黑,由黑變成干枯。時(shí)令告訴人們,紅薯該收獲了……
在故鄉(xiāng),每年農(nóng)歷三月,莊稼人要忙著栽植紅薯。一根根薯藤,扦插在土壤的壟墁上,半月就能長(zhǎng)出一尺、二尺的藤條,半月之后,分枝越來越密,藤蔓越來越長(zhǎng),那些枝葉漸漸地遮嚴(yán)土地。這時(shí)的田野被綠色覆蓋,于是就有了生命力。遠(yuǎn)望,像一片片翠綠的湖面,輕風(fēng)一吹,碧波蕩漾。
在北方,但凡禾谷類的小麥、玉米、高粱及豆菽類的農(nóng)作物,它們的繁育靠一粒粒種子,只要適時(shí)播入土中,就可沖破土層,生根發(fā)芽。紅薯卻另類,它是靠著一根根藤蔓,年復(fù)一年的延續(xù)生命。在我們這里,紅薯是主要糧食作物。在種植上要經(jīng)歷留種——育苗——移栽三個(gè)階段。留種,把當(dāng)年收獲的地瓜,精挑細(xì)選,然后輕拿輕放,小心翼翼地存入生產(chǎn)隊(duì)的大屋窖進(jìn)行恒溫貯藏,以便安全越冬;育苗,次年開春,庫(kù)存的地瓜通過人工二次搬運(yùn),轉(zhuǎn)移到地炕上加溫育苗。火從地生,暖從腳起,其熱融融,紅薯遇熱發(fā)芽,很快就長(zhǎng)出挨挨排排的藤蔓;移栽,清明節(jié)過后,農(nóng)歷三月下旬,正是春茬地瓜最佳栽植期。生產(chǎn)隊(duì)長(zhǎng)統(tǒng)籌安排,各路人馬迅速出動(dòng)。一望無際的田野,盡是忙碌的身影。年長(zhǎng)的莊稼漢手持镢頭,前腳邁一步,后腳跟一步,很有規(guī)則地在壟墁上刨埯,那株距不長(zhǎng)不短,米尺一量,正好三十公分。隨后,增施農(nóng)家肥,挑水澆埯,放置藤條,埋植抹平土墁。
人民公社時(shí)期,種植紅薯就是最主要的農(nóng)事活動(dòng)。農(nóng)民唯一的生活依靠就是地瓜。沒有它,人就會(huì)挨餓,就難以生存。自從把藤蔓栽到地上起,莊稼人就眼巴巴地看著它成長(zhǎng),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根根藤蔓上。
整個(gè)夏季,地瓜生長(zhǎng)期的管理是不敢放松的。莊稼人要把心血與汗水揮灑到黃土地里。當(dāng)?shù)毓涎砼罎M坡,人們就隔三差五地下地勞作。手中的桿子不停地左右翻動(dòng),把藤蔓扎下的根高高挑起,這樣有利于集中力量結(jié)大瓜。秧子翻過,再去除雜草,防止與地瓜爭(zhēng)養(yǎng)分。當(dāng)炎熱而漫長(zhǎng)的夏季過后,地瓜進(jìn)入成熟期。壟上壟下,全是干裂的口子,從裂縫中可清晰看到下面的紅薯,看到新的希望所在。
地瓜收獲季,大約一個(gè)月時(shí)間。裝滿地瓜的地排車車隊(duì),從田間運(yùn)到村里,一部分入庫(kù)大屋窖。另一部分留在地里擦成瓜干原地晾曬,然后交售給國(guó)家。剩下的一點(diǎn)點(diǎn)才分配給農(nóng)戶食用,當(dāng)作過冬的食糧。待地凈場(chǎng)光,農(nóng)家的孩子們挎著杈頭下地?fù)萍t薯。他們手執(zhí)小镢頭,在涼嗖嗖的秋風(fēng)中刨啊,翻啊,一遍又一遍,把落下的地瓜一個(gè)個(gè)找回來。從秋到冬,再到來年春天,田野里盡是青少年弓腰駝背的身影。他們的勞動(dòng)所得,無疑是在幫助家人補(bǔ)給短缺的食糧。
在我生命最初的十幾個(gè)春夏秋冬里,我吃著地瓜長(zhǎng)大,因此與紅薯結(jié)下了不解之緣,終身念念不忘。艱難的歲月里,是紅薯讓我讓鄉(xiāng)親們填飽肚子,維持生計(jì)。紅薯,成了那一代人的救命稻草。
飲水思源。人們永遠(yuǎn)不會(huì)忘記把紅薯從國(guó)外引種到中國(guó)的陳振龍。有關(guān)資料記載:明萬歷年間,福建省福州府長(zhǎng)樂縣有個(gè)名叫陳振龍的讀書人,科舉不第,轉(zhuǎn)而經(jīng)商,往來于福建和呂宋(明時(shí)即菲律賓)之間。在呂宋,陳振龍發(fā)現(xiàn)紅薯藤隨栽隨活,就截取了幾尺莖葉,切成小段,想把它帶回福建。當(dāng)時(shí),菲律賓明文規(guī)定禁止紅薯出境,陳振龍便把薯藤編到纜繩里,經(jīng)過七天七夜航行,在萬歷二十一年五月下旬帶回福建廈門。陳振龍?jiān)谧约以嚪N成功,后請(qǐng)求官府推廣。
清朝時(shí)期,陳振龍的五世孫陳川桂,于康熙初年將紅薯引種到浙江,他的兒子陳世元又帶著晚輩赴河南、河北、山東等地推廣。紅薯種植面積達(dá)到一億多畝,成為僅次于稻米、麥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糧食作物。一根薯藤拯救了中國(guó)三億多人口。
在當(dāng)代,雜交水稻之父,“共和國(guó)勛章”獲得者袁隆平,從20世紀(jì)60年代開始,把畢生精力用在了雜交水稻的科研攻關(guān)上,水稻畝產(chǎn)超過1000公斤,養(yǎng)活了半個(gè)中國(guó)的人口。他還向亞州、非州一些國(guó)家推廣雜交水稻三千萬畝,靠一粒種子改變了世界;農(nóng)民發(fā)明家李登海,被稱為雜交玉米之父,30多年間,先后選育玉米高產(chǎn)新品種80多個(gè),7次開創(chuàng)和刷新了中國(guó)夏玉米的高產(chǎn)記錄。
當(dāng)人們衣食無憂的時(shí)候,怎能不感恩黨,感恩那些為糧食生產(chǎn)做出巨大貢獻(xiàn)的功臣們?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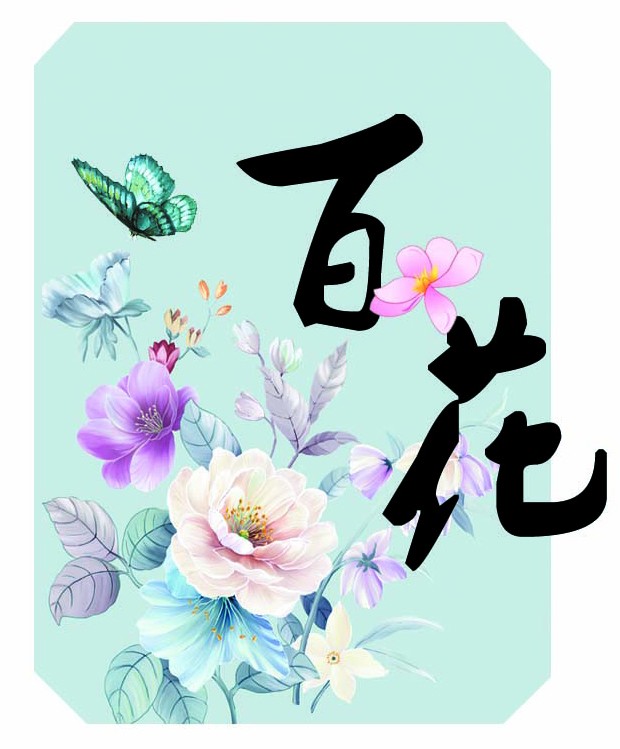


 魯公網(wǎng)安備 37048102001001號(hào)
魯公網(wǎng)安備 37048102001001號(hào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