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楊建東
一種氣味、一首歌曲、一個時令,都能突然勾起我對往事的回憶。仰望藍(lán)天白云,俯視秋風(fēng)拂草,我就憶起故鄉(xiāng)的秋色。
1969年學(xué)校放秋假,姐領(lǐng)我回大塢袁村看奶奶,村外的空氣中彌漫著一股特殊的香氣,那是即將收割的紅麻散發(fā)的香味。那時農(nóng)村是集體生產(chǎn)制,太陽一露臉,社員們扛著農(nóng)具聚集在大街上等著隊長派活,我和叔伯弟跟著大人掰棒子、刨落生,見大個頭的落生就偷偷往衣兜里裝,帶回去給奶奶吃。大人們看見也不吱聲,大伙的身上都流著一個祖先的血,再說我是外地來的小孩,偷二斤三斤落生大人也裝著看不見。掰棒子不是好活,又熱又累,奶奶心疼孫子,不叫我下地。
我跟著一群孩子下河洗澡,村南的大沙河又清又淺,光溜溜地躺在沙灘上,秋風(fēng)拂身,涼爽極了。臥看藍(lán)天浮云,大雁南飛,北山綿延,心里真舒坦,在城里哪能享受這樣的人間樂趣?秋天的莊稼味、土味、草味、水味、風(fēng)味、雨味確實與夏天不一樣。夜里,鄉(xiāng)親們都舍不得點油燈,聚到村西的石橋上聊天,云山霧罩,牛鬼蛇神,無所不聊。河里的明月比天上的月亮還亮,大伙的笑聲震得水中月一顫一顫的,月上中天,人們陸續(xù)回家,曲終人散,只剩“長溝流月去無聲”。
我的記憶像石碑,歷史老人用刀子把故鄉(xiāng)的“三秋”、小孩下河、大隊分糧以及原野上的秋陽、秋風(fēng)、秋水、秋味精細(xì)地刻在石碑上,54年的春風(fēng)秋雨也未把石碑上的圖案風(fēng)化風(fēng)蝕。如今回到故鄉(xiāng),藍(lán)天白云沒變,秋風(fēng)沒變,莊稼的氣味沒變,遙望村北的群山,青山依舊在,幾度夕陽紅。村貌變了,確實是新農(nóng)村建設(shè)的新容貌,街上有許多政府投資的惠民設(shè)施。我感覺最大的變化是人,54年前上工時滿街筒子的扛著農(nóng)具準(zhǔn)備一起下坡的人、吃飯時人們端著碗蹲在街上邊吃邊聊、夜里聚在橋上談鬼拉狐的情景永遠(yuǎn)找不到了。年輕人外出了,老人跟去看孫子,大門上鎖,土地暫租,更讓我嗟嘆的是舊時小友皆是白霜蓋頭的老翁,好幾個已無可奈何地走在黃泉路上。
春去秋來,日升月落,半個世紀(jì)過去了,我們的村子由歷史的車輪載著向繁榮富裕的路上奔馳,農(nóng)業(yè)現(xiàn)代化的神奇代替人工稼穡,因此有許多人外出務(wù)工,50年前的人眾熱鬧的氣氛也被帶走了,給村子留下無可奈何的清靜。說不清什么原因,我對故鄉(xiāng)的秋天回憶一直停留在少年時見到的秋景,可能是那時“農(nóng)業(yè)學(xué)大寨”的沖天干勁、勞動熱情鼓舞著農(nóng)村熱熱鬧鬧忙“三秋”的場景烙在我腦海里50多年沒降溫、沒冷卻。也好,50多年前故鄉(xiāng)忙秋的場景就像一幅老照片,我拿這幅老照片與今天的故鄉(xiāng)秋景來個新舊對比,只是,秋的氣味永遠(yuǎn)不變,秋風(fēng)中的天籟之音永遠(yuǎn)不變。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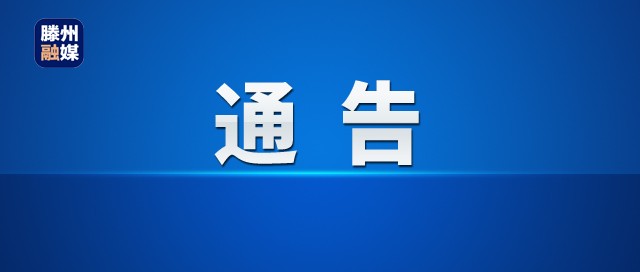
 魯公網(wǎng)安備 37048102001001號
魯公網(wǎng)安備 37048102001001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