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燕開良
清風徐徐,艷陽高照,我駕車前往故鄉(xiāng)燕莊。車飛快地奔馳在北留路上,隔著車窗玻璃,我看到了路兩邊的麥田,金色的麥浪隨風翻滾著,猶如在大地上抖動一床碩大的黃色絨毯。我心情舒暢,不由得放下了車窗玻璃,瞬間飄進來陣陣小麥的清香。麥子熟了的情景,勾起了我對生產(chǎn)隊時期收麥子的回憶,殷殷之情洋溢于筆尖。
五十多年前,農(nóng)村還處在人民公社時期,土地屬于生產(chǎn)隊集體耕種、集體收獲,“三級所有,隊為基礎(chǔ)”,農(nóng)民以生產(chǎn)隊為單位參加集體勞動掙工分,生產(chǎn)隊按工分的多少分配糧食,按勞分配,生產(chǎn)隊長就是生產(chǎn)隊里的當家人。記得,每年麥子抽穗、灌漿的時候,生產(chǎn)隊就安排護坡人員保衛(wèi)麥子。看坡的人晚上到麥田邊巡邏,白天做一些稻草人插在麥田里,驅(qū)趕偷吃麥穗的麻雀。星期天,我們在河畔、坑邊、地頭割草或放羊,累了餓了時,就趁著護坡人不注意鉆進麥地,掐幾穗綠頭麥穗,坐地上搓去麥芒,吃點麥仁打打牙祭,有時也掐兩把到河堤下用火燒去麥芒,再烤一會,搓去麥殼充饑。
麥子成熟的時候是一大景觀,田野里一片金黃,麥浪翻滾,麥穗飄香,只是那時候餓著肚子無心賞景,身在景中不識景,但看著顆粒飽滿的麥穗心里很踏實,有點望梅止渴的感覺。收麥子是農(nóng)村一年中第一場大戰(zhàn)役,一般提前一個月做準備。生產(chǎn)隊要先碾軋一大塊曬麥、脫粒、揚場的打麥場。其場地,有的年份是空閑地,有的年份是生產(chǎn)隊初春種植的菜地。若是菜地,就需要先收割青菜分給各家各戶,然后整平,灑上水,鋪上麥穰或麥糠,幾個勞力拉著碌碡碾軋幾遍(若忙時,抽不出勞力來,就用牛拉著碌碡碾軋,但因牛踩踏地面,一般不用牛),才成為地面質(zhì)硬平滑的打麥場。場里有幾間屋,叫場屋,備有足夠的杈子、掃帚、木锨、車輛、麻袋、繩子等農(nóng)具。各家各戶準備好鐮刀、草帽(席夾子)、茶具,再做些好吃的。一旦麥子熟好“開鐮”,就要晝夜不停地搶收,也叫“虎口奪糧(趕上天下雨,就雨天搶收)”。小麥開割前,生產(chǎn)隊長對隊里所有勞動力進行合理分工,有力氣的主要勞力去收割、裝運。一般情況下,三個割麥的人為一組,中間那個人在前面割(拱壟),并打腰子(打結(jié)),后面的兩人把割的麥子放到腰子上,捆成麥個子,不需要專人捆麥子。打麥場里也安排部分人員,基本上是體質(zhì)弱的婦女勞力,負責護理場間,把場邊的防火大缸都灌滿水,閑時幫著運麥的卸車,并把拉到麥場的麥子晾曬好,隨時軋(輾)麥脫粒。隊長還要安排兩人負責燒水、送飯。收麥時學校放兩個星期的麥假,讓小學生也參加收麥戰(zhàn)役,那可真是男女老少齊上陣,一片繁忙景象。
隨著隊長“開鐮”的一聲令下,男女勞力每人“一耩子”(一畦三耩子或四耩子;若是地面不平整,有一畦兩耩子的,好澆水)三壟小麥,像攻堅戰(zhàn)的戰(zhàn)場一樣,在地頭一字型拉開了收割小麥的序幕。這時,天空越來越亮,太陽將出未出,陽光還沒有照射在大地上,割麥的人們彎著腰,揮舞著鐮刀,默默地你追我趕,爭先恐后,誰也不甘落后,布谷鳥在空中飛來飛去,“布谷、布谷……”清晰的啼唱聲不絕于耳。前面“拱壟”的人,割到地頭后,也不休息,就幫著后面的人割(迎頭)。后面的人一邊割一邊捆,捆成每捆重約三十斤的麥個子。再后面就有三個壯勞力(一人駕轅子,兩人拉偏套)拉著地排車,把捆好的麥個子用木(桑木)杈子挑到車上,車輪飛轉(zhuǎn),把一車一車的麥個子送到打麥場上。
割麥真的像上戰(zhàn)場,“將士”們個個精神抖擻,斗志昂揚,緊張而有序,只聽到齊刷刷的割麥聲,一耩子三壟還沒割到頭,汗水就已濕透了衣衫。我們小學生在運出麥個子的地里拾落在地上的麥穗,有時候,清晨趁著太陽沒出來,露水打得麥穗潮濕,不掉麥粒,就拉竹筢摟麥,這樣收拾的效率高。等大人割麥累了,休息喝水時,我們小孩才能拿起大人的鐮刀學著割幾把,一般情況下,大人不允許我們割,怕我們不小心砍著腿腳耽誤事。割麥子既需要技術(shù),也需要體力,技術(shù)好、體力棒的社員,割得既快又干凈,放地上也不亂,割出的麥茬也矮。割麥時,彎著腰,左手抓一把麥稈,右手揮舞著鐮刀,摸根迅速割下,連續(xù)幾個小時才能休息一會,體力差的人,是難以支撐下來的。記憶中,我母親是干農(nóng)活的高手,割麥子從來都是領(lǐng)頭的,竟能把許多男勞力撇下很遠。
生產(chǎn)隊割麥子,自凌晨下地,一干就是一整天,上午和下午各休息約20分鐘,喝點水緩緩勁,還要趁休息這會時間磨磨鐮。午飯,生產(chǎn)隊管菜、管湯,一般都是做上一大鍋粉條大白菜,或土豆燉粉條,偶爾有點肉,有時粉條白菜燉豆腐,燒白面湯,隊長派專人挑著送到田間地頭、打麥場等收麥現(xiàn)場。飯是各家自帶的食物:煎餅、菜餅子、窩窩頭……大家相互謙讓一番,有的干脆湊到一塊吃,看上去,都吃得非常香甜。誰家的孩子,就跟著誰家的大人一塊吃飯。飯后休息一會,繼續(xù)割麥、運麥、晾麥……田野里除了金黃的麥子,就是低頭彎腰割麥的人群,鄉(xiāng)間的路上車水馬龍,運麥的車把式們不時地吼上幾聲,活躍氣氛,鼓舞干勁……收麥子大軍一直忙到太陽落山才收工回家。人們勞累了一天,一定會渾身酸疼,但看上去,鄉(xiāng)親們?nèi)詭е陲棽蛔〉呢S收喜悅。
那個年代,由于口糧缺乏,農(nóng)閑時的莊戶人家是不吃晚飯的,但收麥的時節(jié)必須吃,不然沒有力氣起早貪黑的加班干活。青年突擊隊、民兵連的“將士”,他們吃過晚飯后,立即集合加班往打麥場運麥個子,披星戴月,歌聲、勞動號子聲響徹夜空。月光下,我們這些孩子們(一般情況下,夜里不安排學生活)在打麥場里盡情地玩耍,杈子、掃帚、揚場锨都成了玩具。有的拿掃帚捂蜻蜓;有的蹲在木锨上,另一個小孩拉著跑;有的模仿電影中的武打動作:打拳、翻跟頭、打滾;也有的躺在麥垛上談天論地,海闊天空的想象,不知不覺就進入了夢鄉(xiāng)……
麥收時節(jié)的打麥場,一天到晚都是車進車出,人來人往,顯得忙忙碌碌,也非常熱鬧。一般凌晨五點,場間的人就起床攤場,把麥個子相互依著撐起,便于透風、透光干得快,務(wù)必在太陽出來前完成攤場任務(wù)。中午,太陽光直射,烈日炎炎,正是晾曬麥子的大好時機,場間人頭戴席夾子,大約每隔兩個鐘頭就翻場一次,將攤場撐起的麥個子再次翻騰一遍,重新?lián)纹穑岥渹€子均勻地接受陽光,晾透、曬干,到了仿佛要自燃的程度時,生產(chǎn)隊長就安排人,趕緊套牛拉碌碡碾場脫粒。碾場人牽著老黃牛拽著碌碡,在攤平的麥稈上繞了一圈又一圈,不停地碾軋,場中心的麥子容易被轉(zhuǎn)到,碾壓脫粒快,周邊的麥稈要多轉(zhuǎn)上幾圈。干燥的麥稈,被碌碡碾得“噼里啪啦”作響。碾場期間,還要有人把碾過的麥稈翻過來,以防背面碾壓不到。碾場要將麥稈、麥穗與麥粒完全分離,做到顆粒歸倉,這就考驗著碾場人的體力、毅力和耐力。烈日炙烤下,碾場人一天下來,雖頭戴席夾子或草帽,但個個都曬得皮膚黝黑。
碾完場后,要起場,用杈子將碾過的已經(jīng)松軟的麥稈(麥穰)挑到一邊,將留在地面的夾雜麥殼的麥粒用推板推掀集中,用竹掃帚清掃成堆,等起風的時候揚場。揚場人用木锨將夾雜麥殼的麥粒迎風揚起,麥粒較重會垂直落下,麥殼較輕而隨風飄落到下風處,借用風力將麥粒與雜物分離,有人彎著腰用掃帚一遍一遍地掃去落在麥堆上的麥殼、麥葉等雜物。木锨鏟起和揚出時發(fā)出帶有節(jié)奏的聲響回蕩在打麥場上空,驅(qū)走了人們的倦意。沒風的時候,有可能要等到深夜,甚至等到第二天天亮才起風,才可揚場。麥穰垛,一座一座像小山,林立在打麥場的周邊。麥穰可作為飼料喂牲畜,也可以和泥增加泥土的韌性,更可作為燃料引火做飯。
老天總是眷顧莊稼人的,連續(xù)給十多天的好天氣(艷陽天),麥子就收獲入倉,人們都曬得黑黝黝的,男人們上身幾乎都脫了一層皮,婦女們手上都磨出了老繭,有的起了血泡。有付出,就有收獲,終于迎來了激動人心的時刻:生產(chǎn)隊留夠交國家公糧的麥子,同時留足麥種和集體儲備糧,剩下的小麥全部分給各家各戶。記憶中,起初生產(chǎn)隊用粗長的木桿秤稱麥子分配,后期用磅秤稱。社員們領(lǐng)到了小麥,都喜上眉梢,笑得合不攏嘴,有的一口袋(麻袋)一口袋地往家扛,有的用地排車或獨輪車往家運。運回家的麥子,反復(fù)晾曬后裝滿了大缸小盆,收獲的喜悅,寄托著代代農(nóng)人的希望。記得當時農(nóng)村說媳婦相媒,女方家除了看男方家的房屋外,還要看糧囤里是否有余糧,主要看小麥有多少,麥子是農(nóng)民的家藏“黃金”,是細糧,麥子多,女兒嫁過來不挨餓。
如今,社會發(fā)展了,時代進步了,農(nóng)村割麥用大型聯(lián)合收割機,直接出麥粒,麥秸稈粉碎還田,讓土地更加肥沃。生產(chǎn)隊時期那原始落后且低效的勞作方式已成為歷史,貓著腰揮鐮割麥、牛拉碌碡脫粒的故事,只能冷漠地出現(xiàn)在子孫后代的書本里,永遠像魂靈一樣孤寂地游蕩在田野上。鐮刀、碌碡、打麥場失去了原有的功能,退出了歷史舞臺,定格成了滿滿的鄉(xiāng)村年代記憶和濃濃的鄉(xiāng)間原始符號。但那收麥子的熱鬧場景一直在我心里,每到一年一度收麥子的時節(jié),那快樂的場景就會浮現(xiàn)在我的眼前,揮之不去,成了我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回憶!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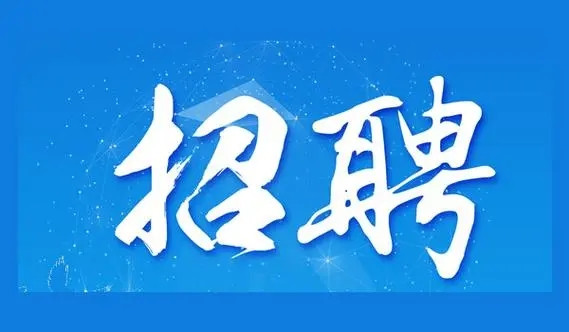
 魯公網(wǎng)安備 37048102001001號
魯公網(wǎng)安備 37048102001001號
